聂辉华(中国人民大学)
每年6月底到7月初,正是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,总有人会向我这个大学教授咨询选大学或选专业的问题。不过,跟前些年相比,这几年奇葩问题越来越多了。比如,有家长问,文科是不是靠死记硬背?还有家长问,听说家里没背景就不适合学经济管理?我不知道(其实知道)这股污名化文科的歪风从何吹来,但总希望有一些专家出面澄清这些对文科的误读甚至是亵渎。
前几天,我拿到马亮教授的新书《学术祛魅:实证研究十讲》(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25年版),觉得这可以成为一本为文科“正名”的著作,虽然作者的本意可能是为文科“祛魅”。这本书从实证研究的角度,详细地介绍了社会科学是如何做研究的。简单地说,解释了为什么社会科学可以称为“科学”。这里说的社会科学,是狭义的“文科”,包括经济学、法学、社会学、管理学和政治学等学科,不包括文史哲等人文学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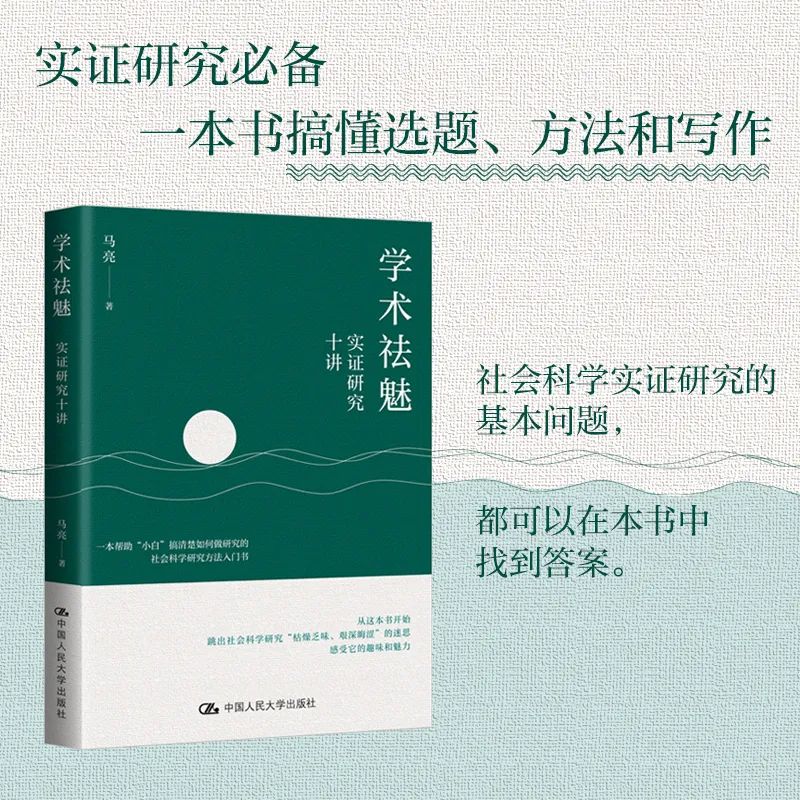
在内容安排上,本书先介绍了什么是实证研究方法,然后顺次介绍如何寻找好的研究选题,如何撰写文献综述,如何构建理论,如何测度变量,以及如何进行研究设计和数据分析,最后还介绍了学术规范与研究伦理。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,这些都是科学研究必备的技能,不仅适用于社会科学,其实也适用于自然科学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文科中的社会科学,是可以称为“科学”的,因为它是靠逻辑和数据说服人的,不是靠死记硬背的!
这样说也许有点抽象,让我举个例子。马亮教授在书中提到,中国基层很多单位,正式编制可能有20个,但是雇佣的编外人员(劳务外包或临聘)可能有上百个,这就有点令人奇怪。更令人奇怪的是,稀缺的20个编制还没有用完,只用了15个。为什么在编制高度稀缺的体制内单位,有正式编制不用,却大量雇佣编外人员呢?这个编制倒挂的现象蕴含了一个有趣的政治经济学问题。我一向认为,“中国的问题,归根结底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”。试问,这样的社会科学问题,能用死记硬背来分析吗?
当然,实证研究或者量化研究并非新方法,介绍量化社会科学方法的书应该不少。但马亮教授撰写的这本书,我认为值得信赖、值得推荐。原因如下。
第一,马亮教授学术水平高,学术发表好。研究水平高的人,才有资格写教人如何做研究的书。马亮原来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,算是我的前同事,去年调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。国际公共管理学界有所谓的TOP 5期刊,马亮教授在其中的四本顶级期刊(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、Public Administration、Public Management Review、Governance)上都发表过论文,这是国际一流的发表水平。他还兼任知名学术期刊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》的联合编辑,《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》副主编以及《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》编辑。毫无疑问,一个不仅自己能发论文,还能挑选好论文的人,在做研究和写论文方面一定有过人之处。
第二,马亮教授文笔好。研究做得好,还(更)要写得好。畅销书《黑天鹅》的作者塔勒布说过一句有意思的话:社会科学理论的命运取决于其传染性,而不是其正确性。换句话说,文笔好,能引人入胜,才能做到“文以载道”。马亮教授不仅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学术论文,而且发表了几百篇评论文章。当年,我们一起在某国家高端智库共事时,我戏称他为“神笔马亮(良)”。因为他写的文章太多了,以至于某年奖励评论文章(非学术文章)时,我不得不专门规定一个奖金上限。这个上限,就是为了给马亮教授“限薪”。
第三,马亮教授长期讲授相关课程,有丰富的教学经验。虽然在顶级期刊发表论文的人不少,但是能给别人讲清楚如何撰写并在顶级期刊发表论文,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。马亮在人大和北大任教时,都曾给本科、硕士和博士三个层次的学生讲授《学术规范和论文写作》课程。我相信,他一定收获了很多好评以及反馈意见。
第四,马亮教授拥有很好的跨学科背景,因此本书的通用性很强。论量化分析,经济学肯定在社会科学中独占鳌头。但马亮教授不是经济学者,他是公共管理学者,其研究领域涉及数字政府、政府创新和绩效管理。如果公管学者都能成功地普遍使用实证研究方法或量化分析方法,那么其它社会科学的学者也可以成功借鉴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非经济学者传播如何进行量化研究,比经济学者传播更有说服力。
当然,本书除了量化分析,其实还介绍了定性研究。例如,他在本书中介绍了如何使用“定性比较分析方法”(QCA)来进行多案例研究。他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:为什么不同地方对于网约车的管制程度不同?以我的观点,会将地方政府对待网约车的现象解读为政企关系,那么为什么有的地方出现了政企合作,而有的地方出现了政企合谋呢?有兴趣的读者,请查看本书相关章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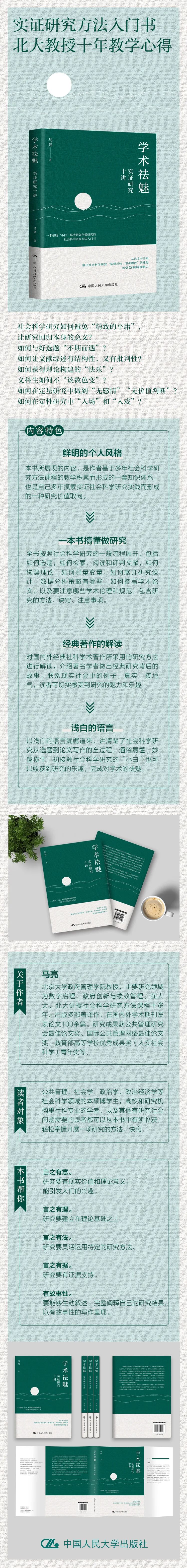
0
推荐




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
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